特佐普洛斯:让戏剧聆听时代之声

《俄瑞斯忒亚》剧照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黄红华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虫鸣突起,神秘的气息迅速弥漫开来。舞台上,一支尽显仪式感的队伍缓缓行进着,一场辩论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不久前希腊国家剧院在会昌戏剧季003上演出的《俄瑞斯忒亚》。这部由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创作的悲剧经典作品,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完整古希腊悲剧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希腊国宝级导演、国际戏剧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西奥多罗斯·特佐普洛斯带领希腊国家剧院的演员们,精心打造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盛宴。
雕塑般俊美的演员、控制力几近极致的身体、仪式感拉满的队形与动作、被抛弃的麦克风、古朴的圆形舞台……会昌老乡与来自外地的观众一道,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共享这一艺术盛宴。
《俄瑞斯忒亚》的故事简单又复杂。阿伽门农带领希腊联军赢得特洛伊战争后凯旋归来,却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及其情人埃癸斯托斯(阿伽门农的堂兄弟)谋杀。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动机既包含对女儿之死的怨恨——阿伽门农曾献祭自己的女儿以求军队顺利出征,也与埃癸斯托斯家族与阿伽门农父辈的世仇有关。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成年后为父报仇,杀死篡位者埃癸斯托斯和母亲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但弑母罪行使其陷入精神崩溃,被复仇女神追杀。俄瑞斯忒斯逃至雅典,接受由雅典娜主持的公民陪审团审判……
2024年,《俄瑞斯忒亚》在希腊埃皮达鲁斯剧场——现存最古老的古希腊剧场里首演。2025年初夏,它来到在中国南方一个偏远小县城——会昌,让这里与世界连接。会昌戏剧小镇赖家老屋广场前搭出一块圆形空地,短暂化身古希腊剧场。小镇街头巷尾,中国的观众与来自希腊的演员们偶遇,相谈甚欢。有希腊演员表示,不舍得离开中国。
在《环球》杂志记者对特佐普洛斯导演的专访中,他不仅畅谈自己对于古希腊戏剧的理解,也强调戏剧在当下的存在价值,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中国观众不吝赞美的感激。
古希腊戏剧的永恒价值
《环球》杂志:在你看来,古希腊戏剧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生命力、依然能够引发强烈共鸣的奥秘是什么?
特佐普洛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内核从未发生改变:激情和冲突——这些最根本的人类经验是永恒的;复仇、正义、命运、尊严、道德挣扎等主题,永远保持着其当下性,在每个时代一次又一次地经受洗礼。这就是伟大的经典戏剧和传统不会面临消亡风险的原因,它们如江河般不可断绝。悲剧叩问的正是那些人类根本无解的问题,直击永恒困扰人类的困境。
《环球》杂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些古希腊剧作家为何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特佐普洛斯:我深信,他们的作品堪称一册独特典籍——既深谙人性之幽微,又洞悉推动历史进程的政治社会洪流,既能感知神话所承载的宏大象征与原型力量,更以炉火纯青的技艺将这一切淬炼为诗。他们之所以显得具有预见性,是因为他们始终洞见并聚焦于我们之前所述的亘古不变、超越时空的人类本质:那些潜藏在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悲剧性缺陷、矛盾、困境与暴行。
《环球》杂志:在古希腊悲剧人物中,你最偏爱哪一个,为什么?
特佐普洛斯:对我来说,埃阿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主将之一)是最独特、最吸引人的角色。雅典娜让埃阿斯陷入癫狂,使他的眼睛蒙上迷雾,所见一切皆非真实。埃阿斯所经历的现实模糊、癫狂状态、力量与脆弱的交织、被压抑的暴力、异化以及觉醒,都是令艺术家着迷与兴奋的创作素材。
《环球》杂志:你最近的作品,比如《俄瑞斯忒亚》和《等待戈多》,都融入了一些当代战争元素。为什么把这些元素融入其中?
特佐普洛斯:首先,冲突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人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与神都存在冲突。冲突是悲剧、戏剧乃至艺术的基本元素。很多时候,有些戏剧本身就是在战争时期出现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战争相关。我认为,艺术家必须与他们的时代连接,并且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恶事,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反思。
我第一次在戏剧创作中涉及战争是1988年在海纳·穆勒编剧的《美狄亚材料》中。我把科尔基斯(美狄亚故事的发生地)设置为战场,当时就有一些国家爆发了战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大屠杀之后。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创作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当时被摧毁的特洛伊城已成一片废墟。

《俄瑞斯忒亚》剧照
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剧场
《环球》杂志:你在今年世界戏剧日致辞中提问:戏剧能否聆听到我们所处时代发出的求救之声?戏剧是否对21世纪的人类困境感到忧虑?戏剧能否不顾虑尚未愈合的创伤,实现其工作坊的职能,使差异可以和谐共存?对于这些问题,你心中有怎样的答案?
特佐普洛斯:我的意图是让这篇致辞成为一个邀请:请对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问题和威胁进行反思,并探讨戏剧如何与之建立连接。生态威胁、人类的机器化和感官的迟钝、我们试图忽视的那些仍在流血的伤口……我不是要给出答案、指示或撰写宣言,而是呼吁要不断地提问、反思和怀疑,并且向狄俄尼索斯求助——这位戏剧之神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具包容性的神,他将所有对立的特性都统一起来——让他成为我们的指引者。
《环球》杂志:在当下这个时代,戏剧的意义是什么?创作者为什么要创作?观众为什么要走进剧场?
特佐普洛斯:戏剧回应了自古以来普遍且永恒的人类需求。“玩”是我们从童年起就天然具有的需求,它是一种娱乐、放松,培养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过程,并能让深不可测的真理得以表达。同样永恒的是讲述故事以及与神话连接的需求。当然,戏剧演出所营造的魔力与激情空间,以及演员和观众之间创造的互动,也具有永恒性。
《环球》杂志:当今世界进入了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观众为什么愿意坐在剧场里看一部长达3.5小时的古希腊戏剧?
特佐普洛斯:在这样一个崇尚“速食”、数字化令分心成为常态的时代,静静地坐下来观看一部3.5小时的戏剧,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抵抗——一个人性化的宣言,对抗异化的精神姿态;也是重新与戏剧的仪式感连接的一种象征行为;还是对演员们挣扎与超越的礼赞,一次向内探索的约定——观看演出的过程,意味着观众与演员们一同踏上了超越自我的精神之旅。
构建剧场的仪式感
《环球》杂志:你导演的古希腊戏剧,要么在古希腊剧场演出,要么构建一个类似古希腊剧场的舞台。此外,你的舞台都很质朴,不使用多媒体等复杂技术,比如演员尽量不戴麦克风。这些仪式感想要传达什么?
特佐普洛斯:出于许多实际和象征性原因,圆形露天剧场是古希腊戏剧表演的理想场所。在露天圆形剧场中,演员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的集体感知体验都被放大了。露天圆形剧场确保了最优的声音效果,因此,只要演员们经受过声音训练,他们就无需麦克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封闭的室内剧场,只要它们符合某些条件即可。对于最简朴的舞台设置来说,我认为演员居于舞台中央是戏剧的基本条件。我所说的演员,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力以捕捉灵感,身体和声音皆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对外界刺激保持开放,高度专注,沉浸于当下的时空场域,但同时又能游离在另一个维度。此外,简朴而几何化的舞台设置,为歌队的表演提供了可能性——歌队代表集体,而集体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在我们的演出中,歌队的队形也保持几何化,因为几何化给激情以尺度,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创造和谐。强烈的几何形态塑造了强烈的记忆。
《环球》杂志:在你的戏剧作品中,演员展现出超强的控制力、能量与信念感,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演员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特佐普洛斯:实际上,这种方法是通过一系列训练达成的,包括养成腹式呼吸习惯、强化身体轴线、解放声线以及放大能量等。通过这些训练,我们逐步实现如下功能:解构、持续的即兴创作(也许是最能让演员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以及台词的韵律化表达。而且,除了加强练习之外,这一方法的形成因素还包括演员的专注力,以及戏剧本身具有的时间概念、祭奠仪式起源和表演魅力。最终,通过这些训练,演员得以展示他们作为一种创造性和精神性的存在。演员经常对他们身体和声音的可能性感到惊讶,惊讶于随着训练的深入,疲惫感逐渐消退,而能量感持续增强,他们也惊讶于自身创作能够达到如此的深度。

特佐普洛斯导演
戏剧将不同文化连接在一起
《环球》杂志:你的作品中,《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由希腊、土耳其和德国的演员演出,《等待戈多》是和意大利演员合作,《俄瑞斯忒亚》由希腊和意大利演员演绎。你为何偏爱这种跨国家、跨文化的创作呈现?
特佐普洛斯:我更愿意称之为“文化融合”,这是我40年来一直坚持的创作方法。我对不同的语言、戏剧传统和神话故事感兴趣。不同的语言让我着迷,尤其是每种语言中元音和辅音的节奏和发音。与不同国家和戏剧传统的演员合作,让他们不摒弃自身的戏剧传统,同时试图将另外一种戏剧风格灌输给他们,这是一种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比如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你必须让来自不同国家和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演员阵容组成一个和谐且同质化的整体。我相信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我的表演方法:日复一日地在团队中创造出集体感、共同的戏剧语言和最终统一的思想体系。
《环球》杂志:你的戏剧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东方戏剧元素。东方戏剧尤其是中国传统戏剧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特佐普洛斯: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祖先曾被逐出故土本都(位于黑海南岸的一个古代王国)地区。我在本都的传统、故事和叙事中长大,甚至,那些源自东方的深层的潜意识里的记忆,通过我祖母吟唱的歌谣和讲述的故事,深深地刻入我的基因。我认同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说法,“希腊是亚洲浪潮的最后一波”。古希腊与东方曾展开深刻的文化对话,古希腊的艺术与哲学吸纳与融合了许多东方元素。所以,不必讶异,我对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戏剧,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我觉得,对于空间、时间、象征主义等概念,我们有着相同的传统和起源。
《环球》杂志:《俄瑞斯忒亚》在会昌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你的团队要求第二场把观众席照亮一些——演员在表演中需要看到观众的反应。你觉得舞台上下是怎样一种关系?
特佐普洛斯:在中国表演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有启发性的经历。它向我们展示了悲剧如何超越时间将不同文化连接在一起。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中国的观众中有特别多的孩子和年轻人,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观看演出。《俄瑞斯忒亚》在会昌首演后的几天,我们的团队在街头遇到一些中国观众模仿歌队的动作,这显示我们都成为某种非凡存在的一部分。会昌戏剧季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对于被邀请演出,我们由衷地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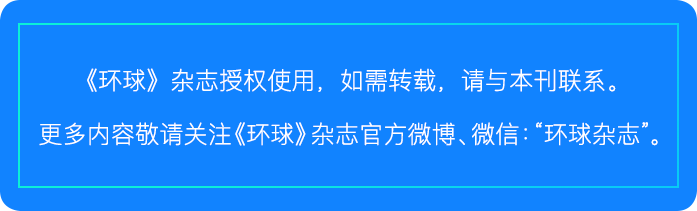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